上海校园餐背后的供应商,越挖越让人心惊! 上海校园餐问题 上海校园餐
上海校园餐巨头绿捷的业绩,让我想起了马兰德隆版《佐罗》的开场镜头:一个玉米小贩在广场上热情叫卖“猪能吃,人也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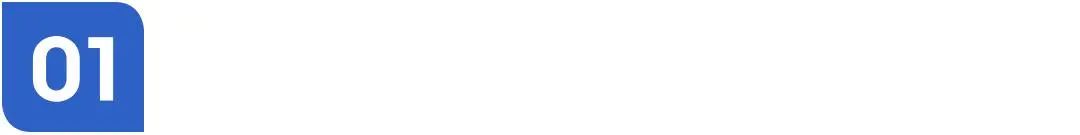
一份虾仁炒蛋把上海绿捷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其实,这事在网上发酵有几天了。事发时全网围观罗永浩暴捶西贝,没啥热度。甚至在事件爆发之初的9月14日,家长在网上发文呼吁“希望西贝参与竞标上海中小学学生餐”,还得蹭罗永浩的流量。
9月15日,上海部分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称,孩子所在学校午餐中的虾仁炒蛋有异味,被紧急停止供应。后经媒体调查曝光,虾仁炒蛋的供应商是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如果只是虾仁炒蛋的偶然翻车,事情也不至于闹这儿大。实际情况却是“苦绿捷久矣”的舆情汹涌、槽点满满。有家长向媒体记者反映,其孩子的校园餐的供应商正是上海绿捷。“多次听孩子吐槽难吃,且有家长反应多次,但供应商均未更换”。社交媒体评论区的海量吐槽,也能佐证了这位家长的观点。更有媒体爆料、网友深挖绿捷历年的投诉记录和诉讼记录,不完整但不少。

9月18日更是来了一波高潮,虾仁炒蛋只是冰山一角。魔都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有开放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记者通过该平台对上海绿捷公司进行了查询。结果显示,上海绿捷公司进购的肉品中包括多款保质期365天的冷冻鸡鸭肉和鱼类、保质期540天的冷冻牛羊肉,以及保质期720天的冷冻五花肉。
难怪事发时家长们要呼唤“西贝参与竞标”,与绿捷超长待机的僵尸肉相比,网传西贝的“两年生”西兰花是真香……
好吧,“真香”是夸张了,但是至少它不臭啊?
更出人意料的,是绿捷的背景。经各路媒体的深入挖掘,绿捷的复杂“身世”曝光。绿捷的背后是四川的新希望集团——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养猪业巨头。全年饲料销量2596万吨,位居世界第二,出栏生猪1652.49万头,位居中国上市猪企第三。
正是绿捷特殊的“身世”引发了本文开头的联想。

调侃归调侃。英雄不问出身,主营饲料和养猪的企业跨界校园餐也很正常。毕竟食品工业、餐饮业是非常成熟的产业,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但是,绿捷的成功太异常了。
校园餐生意的现金流稳定,还自带餐费预收的现金池,还容易有规模效应,是门好生意。凡是好生意,都是竞争都激烈的“王者局”。上海及周边长三角城市的餐饮业、食品工业高度繁荣,强手如云。能入“局”的更是王者中的王者。按理说,绿捷既是外来的“过江龙”又是跨界转行的餐饮业新手,在这样的高端局里总得猥琐发育一段吧?然而,并没有。
绿捷,出道即巅峰。
2014年注册成立,2017年就以日供36万份校园餐的骄人业绩,一举成为上海市中小学生最大的营养餐供应企业。目前更是增加到了日供50万份,“王者局”的至高王者,名副其实的高处不胜寒。
可别小看这10多万的增长。众所周知,上海是少子化的重灾区,中小学生校园餐饮市场几乎没有增量。猪栏里的猪没增加,能把饲料卖得更多了,就得有真本事。
就在事发前的8月,绿捷还大规模扩张了一波,密集中标27个项目,覆盖超500所学校。如果不是这次虾仁炒蛋的惨祸,绿捷一统上海校园餐指日可待。
绿捷凭什么能成为压倒众多“地头龙”的速成王者,是个迷。这还得从校园餐的产业特征找原因。
校园餐生意是好生意,但准入门槛高、监管严。准入门槛高,不仅对企业资质有很高的要求,拦住了大部分中小餐饮企业,还对利润有严格的限制。提高准入门槛,无疑符合主流民意。大众印象中,中小餐饮鱼龙混杂,安全隐患更多,当然要限制规模。限制利润更是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校园餐有公益属性,更要限制“万恶的利润”。所以,校园餐的招投标会根据地段不同严格计算成本,对不同区域的学校有15到25元的餐标细分,账算得非常之细。
监管严,更是从民所请的层层加码。本来食品餐饮就是监管的重中之重,“婆婆”多、规矩多。校园餐比其他商业餐饮增加了教育部门从上到下的全套,以及家委会等意见反馈的自下而上。甚至上海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还辟有专门的通道。
可以说,校园餐市场是最符合中国大众“严格监管”想像的完美理想模式。可是,校园餐桌的事故率不低,出的都是低级事故:
2023年,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鼠头鸭脖”事件,成了全球互联网玩梗的现象级事件。
2024年,河南三门峡义马市第一初级中学上百名学生因食堂食物引发集体食物中毒;湖南长沙中加中学因使用烂番茄和脏桶盛放菜品,导致学生急性肠胃炎;辽宁本溪五里甸学校甚至将准备喂狗的剩菜重新给学生食用。
既然传统食堂伙食团搞不好,那就上科技,中央厨房的预制菜、复热菜进校园,遂有了绿捷的崛起。
科技路线的解题思路是对的,虽然大众对预制菜充满了不信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预制菜更易监管,严监管之下更易实现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实是,世上就没有绕不过的监管。
比如对企业规模的高标准,无非是砸钱扩大规模。花钱能解决的事,就不是事。别说做饲料的,就是收垃圾的也能砸钱跨界校园餐饮。
严控利润的“精细化操作”,实际上只会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本加厉的反作用。你有严控利润的金箍棒,我有严控成本的天灵盖,谁怕谁?现做的可以用剩饭剩菜,预制的可以用僵尸肉。甚至预制的更不怕你“严控利润”,僵尸肉怎么了?保质期三年,我用两年十一个月的“临期产品”,合规性没毛病啊。拉高准入门槛的监管措施,百无一用。
至于学生家长的反馈,学校想管可以管,想不管可以解释。豆腐酸了,那是醋多了。肉有异味,那是孩子敏感了。味道不行,更是众口难调。

别骂学校老师不负责任,他们背着一堆KPI的责任太多了,有心无力。
更何况一天能卖几十万份学生餐的,能是省油的灯?区区一个校长、一撮老师,乃至区县教育行政机构,能管、敢管、管得了?还是有心无力。
连那个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都可以宕机。机器都知道轻重缓急、趋吉避害,何况是大活人呢?
所以,分散管理的传统食堂也好,规模化集中管理的中央厨房也罢,都是管不住的。甚至后者比前者的风险更大、追责更难。
校长二叔的小姨子的二公子亲家承包的食堂出问题,充其量是祸祸一个学校。真闹大了,追责一个校长也不是啥大不了的。
可是,每天出货万计、包了半城校园餐桌的大企业,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真要出问题,一次能撂倒半个城。事后严格追责,涉及的利益链有多庞大,追得动吗?
动真格地处理,庞大的产能替代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一天50万的绿捷,真是“大而不能倒”。试想一下,停了绿捷的供餐资格,哪儿找替代?能替代的未必合规,合规的未必能替代。
严格的准入、苛刻的监管要求之下,每天五十万份校园餐,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找到,让孩子们吃半个月方便面?
9 月18日,上海市教委发文称,“将广泛听取学生和家长意见,加大对供餐企业监管力度”,反应速度不算太慢,至于最终“监管效果”处如何,只能静观后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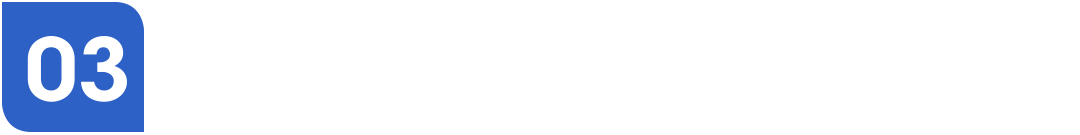
某种程度上来说,像绿捷这类大规模生产的“中央厨房”模式,其实是在所谓“严监管”下诞生的的寡头化垄断,而且是一种逆淘汰产物。
试想一下,绿捷要是真能做出好吃、健康又安全的校园餐,完全可以开成大型连锁餐饮,何必专攻校园?这类在严监管“保护”下的校园餐饮企业,明明是餐饮行业的劣质产能,却在做要求最高的校园餐饮。做出“猪能吃,人也能吃”的东西,岂是意外?
这和预制菜好不好、安全不安全无关,却因蹭预制菜争议的热量大火,挺讽刺的。
校园餐给什么吃什么,和喂猪没啥区别,大众早已安之若素。西贝的预制菜,消费者有权选择不吃,却吵得昏天黑地、义愤填膺,这就更讽刺了。
上一篇:电力现货市场全覆盖倒计时
下一篇:机器人北京上学记
